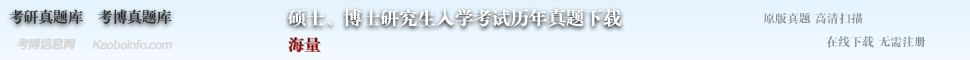一 边缘
那天我为你弹断了琴弦,
从此一个人坠入边缘。
七月流火,淡蓝的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杨树叶子在阳光下变成一片炫目的白光,刚刚上午十点多钟,但隔着窗户就能感觉到室外的喧喧热浪。P大理教117的冷气却开得极足,近五百人挨挨挤挤地坐在一起,我还是感到腰上森森生寒,膝盖也隐隐作痛起来,小腹上更是一片冰凉。我暗暗叫苦,没想到P大的空调这么奢侈,这种日子受凉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身体虽然还行,可每月一次的肚子疼却着实凶险,再被冷气吹一天,晚上只怕要变本加厉。要是换了别的课,我早就逃之夭夭了,可是此时我只是叫一声苦,转了转逃走的念头,就坚决摒弃了那种可耻的想法,决定坚守阵地,毫不动摇,要知道,我现在上的是P大法学院的考研辅导班啊,P大,法学院,还是考研!
这个辅导班着实是来之不易,当我大清早六点钟来排队报班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已经一波三折,居然还有人夸张地带来了马扎,让我不由地联想起我在北外时看到大伙儿排队领托福报名表时的盛况。那大概是99年的夏天吧,领表的头一天晚上,我们东院的小操场就已经人山人海,大家坐在报纸上打牌、吃零食、高声谈笑,显然预备彻夜不休,来迎接天明时那一张“寄托”自己梦想的表格,那光景俨然是一场圣诞夜狂欢派对。
我没有考过托福,却排过三次托福大队,一次是为阿建领,两次是为朋友领,现在阿建还好好地在我的身边,两个朋友则算是成功地飞跃重洋了。
我似乎与排队有缘,托福大队之外,由于我的牙此起彼伏地染恙,我只好欲罢不能地在黎明时分排在魏公村北大口腔医院的大厅里,等所有的牙都治了一圈之后,我也毕业了。而在我毕业仅仅几天之后,我就又排在了P大逸夫壹楼的门口。
现在想来,排着大队辛辛苦苦领来的东西,它的价值多半未必对得起我们的热情,可是在一定的时段里,它太稀缺,而我们又太狂热。大家都想要的东西,想必一定是好的,当年的托福如此,而此时的P大法学院也如此。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花钱得来的东西都只是一种交易。可是当你定了闹钟,天刚麻麻亮就一骨碌地揣着钱来排队,不敢抱怨价钱贵、不敢抱怨队伍长,只求他们肯收下你的钱就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拥有选择权的消费者,而是一个谦卑的追求者了。而正如这场交易关系所显示的,我和P大法学院之间的关系,正是追求者与被追求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以后的数年里,我曾经屡次反思维持这种关系的意义究竟何在,但在这个2001年的夏天,我却是热烈而真诚的。
P大法学院其实并不见得是全国最强的法学院,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最难考的法学院。以P大百年名校的号召力,法律专业炙手可热的吸引力,正可谓简章一出,应者云集,相对于越来越多的追求者,它却从来不扩招,恰到好处地保持着矜持和所谓的含金量,因此也就不怪大家趋之若骛、仰之弥高了。
虽然说报班来之不易,上课十分辛苦,大家的情绪却着实饱满,许多人像我一样都是来自外校、外专业,能和P大法学院的先生们亲密接触,心情几近虔敬。而首位闪亮登场的法理学周教授更是把大家的兴奋激动之情推到了顶峰。法理学这门课本来最不容易讲得有趣,但这位周先生显然深知人心,驾驭有术,轻轻松松地把大家迷得七颠八倒。周先生声名在外,听过先生讲课的同道中人想必不在少数,下面是我顺手捡的几段牙慧,或许大家可以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段子一:学生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学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周先生:哦,这种说法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段子二:某学生给先生来信,赞道“先生乃中国立法学之父……”,先生回信曰“敢问立法学之母安在?”
段子三:某年法理学的考研题目是“试述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一考生见题愤然,提笔云“那种认为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地位很重要的认识,是很糊涂的”。先生览之莞尔,评曰“那种认为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地位不重要的认识,也是很糊涂的。”
段子四:某年考研,一考生考场铩羽,失望之余提笔曰“旺旺、老贺、苏力(注:皆法理学名师),今年我不行了,别了!”先生览卷感慨,评曰“你安心地去吧,会有人继续你未竟的事业……”
段子五:一力促成法国民法典的诞生的拿破仑不但是军事天才,为人也风流多情。在某次戎马倥偬的间隙,他写信给一位贵妇人说:“虽然很忙碌也很疲惫,但我一有时间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谁呢?不告诉你……”
在阵阵欢笑声中,我们下课休息,可能是我神往的样子过于幼稚了吧,我旁边的女孩笑道:“看你就是第一次听周老师的课吧?我可是第三回听到拿破仑的情书了!”
女孩一身浅灰色暗花的套裙,头发烫成大波浪潇洒地披在肩上,眉目间很有些飞扬的意思,只是嘴唇偏薄,紧紧地抿着,显得有点凌厉了。
我有些惊讶,我虽然听说过考P大法学院的人中不乏有连年征战的,但没想到这么俯拾皆是。
女孩眼珠一闪,似乎便看出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我只考了一回,去年听了一次学习班,但我还听过他讲的司法考试辅导班,第一次觉得新鲜,听多了也不过那些东西罢了。”
我这会儿正迷着周先生,听女孩的口气很有些不屑,便觉得她太刁钻了,心想谁让你听三遍的呢。我不曾想到世事难料,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足足听了五遍周先生的辅导课,前四遍是身临其境,最后一遍是听的录音,听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傻了,第五遍听完之后,再无力发表任何评论,而现在想起法理学来,脑中仍是一片迷茫。
我们攀谈起来,女孩名叫胡曼卉,浙江金华人,去年从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北京一家律所打工,今年1月份才考了一次P大法学院,就差一点儿,所以预备再接再厉。
胡曼卉左边坐着一个圆圆胖胖的男孩,脸上稀稀落落的几颗青春痘,这时也凑上来搭话道:“真巧了,我也姓胡,也是浙江人,不过我今年是第一次考,心里太没底了。”
胡曼卉一听有些兴趣,问男孩是哪个学校的,男孩掩嘴胡卢一笑:“小学校,小学校……”
胡曼卉还欲追问,我以为男孩的学校没有名气,不好意思说,于是请教他的大名。
男孩又掩嘴一笑:“名字不好,名字不好,我单字一个gao,gaogao秋阳嘛,不过我的姓不好,合到一起就不好了……”
男孩说话声音既低,说得又快,语焉不清,加上我和他之间又隔了一个胡曼卉,我只听到“不好”、“不好”、“搞搞”,不知道他究竟在搞什么。只见男孩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斗大的“杲”字,本来容易写得方方正正的这个字在他笔下仿佛被风吹过,柔弱无骨地斜扭着身子。
我忍不住笑道:“这个字虽然不常用,但意思很好呀,好像唐朝有个大臣叫做颜杲卿吧,就是这个字。”
男孩脸上顿时一亮,笑眯眯地正要说什么,胡曼卉道:“这么生僻的字!这是念‘搞’吗?你叫胡——杲?啊……哈哈哈哈!”
我不如胡曼卉反应敏捷,听她拖音拉调地念出“胡杲”二字,才明白过来,也不由地笑起来。那个男孩显然早已经习惯了自己名字的娱乐功用,看到两个姑娘发笑,立刻配合地作沮丧状道:“我们这一辈兄弟名字都有个‘日’字边,而且据说我五行缺木,当年我爸他们查了好一顿字典才弄出这么个字来,唉!真不幸啊!姓胡的就是不好起名字。”
胡曼卉撇撇嘴:“这跟姓胡有什么关系?……不过,你知道我们学校搞商法的那位‘饭加菜’教授吧,跟你这名字简直是异曲同工。”
我知道南大的那位范嘉材教授,我现在学的商法教科书就是那位范教授主编的。事涉师长,我本不想妄加评说,但突然想起一个笑话,忍不住说道:“我们本科的时候上经贸学院的选修课,老师年轻英俊,叫做范徵,他说姓范的可难起名字了,他的名字总算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他去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的时候,听到人家一口一个‘professor 蒸·饭’,心里暗暗叫苦,真是百密一疏,防不胜防啊!以后我们就叫他蒸饭教授了。”
无聊的笑话最容易让人亲密,我们三个笑了一回,顿时感觉气氛融洽了好多。胡杲听说胡曼卉考过一次,不放过打探消息的机会,问道:“你考什么专业?你说去年考了一次,差在哪一门上?”
我原以为胡曼卉不会愿意提起考场失利的事情,可她似乎正等着这个问题重温自己失之毫厘的遗憾,欣然答道:“自然是考国际经济法了,本来民商法我也考虑过,可还是觉得不如国经来得实惠。其实我也挺想去当刑事案子的辩护人的,我原来是我们院里辩论队的三辩呢。今年P大法学院分数线是320,够低的了吧?可是分数压得特别紧,快两千个人考试,也就一百多个过线的,剩下的分数那么低,想调剂别的学校都没戏。我考了331,高了十分呢,可是综合一的题目也太变态了,我竟然没及格,连面试资格都没有。”
我和胡杲听了都肃然起敬,我没想到胡曼卉考得这么好,由衷说道:“真可惜,你第一次考就这么厉害,真了不起。今年好像很多人都是因为单科不及格刷下来了。你明年肯定没问题了。”
胡曼卉点点头,嘴上却说:“那倒不敢说。你是转专业的,别着急,慢慢考吧。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反正考五六年的也大有人在。等我考进去了,一定给你透露一些内部消息。”
这时候听胡杲嘟囔了几句什么,胡曼卉叫道:“原来你是西北政法的啊!那你刚才干嘛还藏着?我们虽然学校强,可是我们法学院还真不一定比得上你们呢!”
胡杲脸上放光,意气风发,声音也提高了一档,说:“这倒是的。几个政法大学里,中国政法这几年招生太滥了,华东政法的教授们都去下海扒分了,西南政法的好老师都跑到北京上海了,中南政法本来就不如我们。倒是我们学校还有几个人耐得住性子做学问,这些年发展得还不错。”
我好生奇怪,看胡杲的样子明明很为自己的学校自豪,可是为什么刚才要支支吾吾的呢?于是问道:“那你刚才还说是小学校……”
胡杲嘻嘻笑道:“比起南大来,我们学校确实很小呀!”
胡曼卉淡淡一笑,我突然明白胡杲刚才的“小学校”和胡曼卉的“分数差一点”一样,是要引人来问的。原来是我糊涂,还以为那是人家的短处,其实没准儿人家还嫌搔不到他们的痒处呢。
突然,一声清脆的琴弦声打破了嘁嘁喳喳的嘈杂声,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给大家唱首歌。”这声音虽低却颇有穿透力,仿佛玉珠一颗一颗地掉进金盘里,琤瑽作响,柔和又不失清朗。我愕然抬头,只见一个背着吉他的男孩子正站在讲台中央。
这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孩。他的身材修长,泛白的牛仔裤勾勒出他瘦韧的腰身和匀称结实的长腿,肩膀很宽但略显得单薄,脸色有些苍白,栗色的长发披在肩头。男孩的相貌清秀,但鼻梁和下巴的线条非常英挺,眼睛很漂亮,却隐隐地露出一股侠气。他大方地站在讲台上,仿佛丛林中的一只美丽的花豹,说不出的从容和优雅。
我不由得呆住了。我的相貌普通,本来对这么帅的男孩是不敢多看的。可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男孩时,我就震惊极了。他也许并非英俊得无与伦比,但他的气质像极了我在心中描绘了很多年的主人公——一位唐代的将军。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出一个叫做《白马篇》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历尽坎坷的少年,出塞入塞,从游侠儿成长为一代边塞名将。我把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真和美都加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我的笔墨不足以描摹他于万一,所以我永远也写他不出。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我便分析说,我的主人公只不过是周瑜、曹植、兰陵王、狄青和纳兰容若的大杂烩,是女孩子排遣无聊的一个绮丽梦想。但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沉迷其中。而今天这个素昧平生的男孩一下子狠狠地撞在了我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我又惊又喜,又有些被侵犯了的不安感,很想移开视线,却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看。
男孩轻轻拨了拨琴弦,说:“这是我写的一首歌,叫做《边缘》。”
我在大一的时候学过一阵子吉他,用的是最普通的红棉吉他,只因为学吉他买琴和报班的成本都最低。我学得很差,但有机会听过很多校园歌手的弹唱,觉得大多旋律单调,内容苍白,渐渐也就失了兴趣,开始仰慕古筝和琵琶。可是今天当淙淙的琴声从男孩修长的指下淌出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吉他其实是相当有潜力的乐器,我只是没遇到真正会弹的老师而已。
男孩的声音有一点像许巍,但没有许巍那么沧桑,低沉中还带着年少的清扬:
“那天我为你弹断了琴弦,
从此一个人坠入边缘。
人群的边缘,黑夜里的孤单,
匆匆来去的人们,漠然的脸。
做客京城的这个冬天,
只有风卷尘沙经过我的门前。
……”
舒缓的琴声渐渐地变得激昂起来:
“我身在人群的边缘,
心常飞越华山之巅,
江湖路远,寒山笼烟,
男儿何妨匹马伴青衫。
莫辜负了腰间三尺剑,
何必管明月照向谁边,
了结了今生的心愿。
……”
男孩的吐字非常清晰,歌词一句接一句地撞进我的耳中,我越来越吃惊。如果说前半首歌说的是现代青年人的孤独,那么后半首歌简直就像是武侠片的主题曲了,而旋律上也是前半低沉,后半慷慨。前后两半在词和曲似乎都有些不协调,但男孩缓缓唱来,并不给人突兀之感,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而且男孩所要表达的氛围已经呼之欲出,我俯身写下他的歌词,竟有一种激荡之感。
曲声渐歇,男孩徐徐把琴收起来,一边说道:“如果大家觉得我唱得还可以,可以送给我一块钱,也不必多给,一块钱就行了。”
教室里又响起了嘁嘁嚓嚓的声音,大家不知道在议论些什么,一些人已经开始翻书包找钱了。歌手收钱是很正常的,可是这句话出自这个男孩的口中,令我感到十分意外。从今天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男孩起,我就被他深深地吸引,等我听到他的歌,更觉得似曾相识,但他的歌和气质都透着一股冷傲,虽然让人神往,却很难亲近。这样潇洒的人物谈及钱字,让人不免有些尴尬。
胡杲手里托着两个一块钱的钢蹦,站在座位上,笑嘻嘻地问我们“你有吗?……你有吗?”,我拿出一块钱放在他手中,胡杲看看胡曼卉,指指手里的一个钢蹦说“这个算你的吧!”,胡曼卉撇撇嘴,没有作声。
胡杲又张罗了一会儿,手里握了一把钱,摇摇摆摆地朝讲台走去。送钱过去的人还真不少,粗粗看一下,少说有二三十个,其中不少是像胡杲这样握了一把钱的,可见男孩这首歌唱下来,成果还是让人欣慰的。
这期间男孩一直默默地站着,我没好意思怎么看他,但感觉出他的神色并不太自然,他似乎竭力表现出若无其事或者漫不经心,但有点僵硬的姿势泄露了他的羞涩和紧张。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男孩合上琴套的拉链,大大方方地道了一句“谢谢大家”,背上琴飘然而去。
这是我听到的歌手曹溪的第一首歌,这首歌虽然将我深深地打动,但是它似乎不具备流行的要素,说它古雅也好,说它晦涩也好,反正当数年之后曹溪的歌声传遍大街小巷、他的忧郁与高傲成为少女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的时候,这首《边缘》却永远地湮没在了岁月之中。我曾经找遍了曹溪的每一张专辑,但从未再见过这首歌,仿佛我在2001年夏天的这个上午的所见所闻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但我喜爱这首歌,这么多年来对它一直念念不忘,我常常想,当年听过《边缘》的同学们,是否也会有人在默默地怀念它呢?而我在P大法学院考研辅导班的第一天所听到的《边缘》,似乎竟成了我接下来五年生活的谶语。
一 边缘
那天我为你弹断了琴弦,
从此一个人坠入边缘。
七月流火,淡蓝的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杨树叶子在阳光下变成一片炫目的白光,刚刚上午十点多钟,但隔着窗户就能感觉到室外的喧喧热浪。P大理教117的冷气却开得极足,近五百人挨挨挤挤地坐在一起,我还是感到腰上森森生寒,膝盖也隐隐作痛起来,小腹上更是一片冰凉。我暗暗叫苦,没想到P大的空调这么奢侈,这种日子受凉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身体虽然还行,可每月一次的肚子疼却着实凶险,再被冷气吹一天,晚上只怕要变本加厉。要是换了别的课,我早就逃之夭夭了,可是此时我只是叫一声苦,转了转逃走的念头,就坚决摒弃了那种可耻的想法,决定坚守阵地,毫不动摇,要知道,我现在上的是P大法学院的考研辅导班啊,P大,法学院,还是考研!
这个辅导班着实是来之不易,当我大清早六点钟来排队报班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已经一波三折,居然还有人夸张地带来了马扎,让我不由地联想起我在北外时看到大伙儿排队领托福报名表时的盛况。那大概是99年的夏天吧,领表的头一天晚上,我们东院的小操场就已经人山人海,大家坐在报纸上打牌、吃零食、高声谈笑,显然预备彻夜不休,来迎接天明时那一张“寄托”自己梦想的表格,那光景俨然是一场圣诞夜狂欢派对。
我没有考过托福,却排过三次托福大队,一次是为阿建领,两次是为朋友领,现在阿建还好好地在我的身边,两个朋友则算是成功地飞跃重洋了。
我似乎与排队有缘,托福大队之外,由于我的牙此起彼伏地染恙,我只好欲罢不能地在黎明时分排在魏公村北大口腔医院的大厅里,等所有的牙都治了一圈之后,我也毕业了。而在我毕业仅仅几天之后,我就又排在了P大逸夫壹楼的门口。
现在想来,排着大队辛辛苦苦领来的东西,它的价值多半未必对得起我们的热情,可是在一定的时段里,它太稀缺,而我们又太狂热。大家都想要的东西,想必一定是好的,当年的托福如此,而此时的P大法学院也如此。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花钱得来的东西都只是一种交易。可是当你定了闹钟,天刚麻麻亮就一骨碌地揣着钱来排队,不敢抱怨价钱贵、不敢抱怨队伍长,只求他们肯收下你的钱就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拥有选择权的消费者,而是一个谦卑的追求者了。而正如这场交易关系所显示的,我和P大法学院之间的关系,正是追求者与被追求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以后的数年里,我曾经屡次反思维持这种关系的意义究竟何在,但在这个2001年的夏天,我却是热烈而真诚的。
P大法学院其实并不见得是全国最强的法学院,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最难考的法学院。以P大百年名校的号召力,法律专业炙手可热的吸引力,正可谓简章一出,应者云集,相对于越来越多的追求者,它却从来不扩招,恰到好处地保持着矜持和所谓的含金量,因此也就不怪大家趋之若骛、仰之弥高了。
虽然说报班来之不易,上课十分辛苦,大家的情绪却着实饱满,许多人像我一样都是来自外校、外专业,能和P大法学院的先生们亲密接触,心情几近虔敬。而首位闪亮登场的法理学周教授更是把大家的兴奋激动之情推到了顶峰。法理学这门课本来最不容易讲得有趣,但这位周先生显然深知人心,驾驭有术,轻轻松松地把大家迷得七颠八倒。周先生声名在外,听过先生讲课的同道中人想必不在少数,下面是我顺手捡的几段牙慧,或许大家可以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段子一:学生甲: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学的书上是这么说的……
周先生:哦,这种说法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段子二:某学生给先生来信,赞道“先生乃中国立法学之父……”,先生回信曰“敢问立法学之母安在?”
段子三:某年法理学的考研题目是“试述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一考生见题愤然,提笔云“那种认为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地位很重要的认识,是很糊涂的”。先生览之莞尔,评曰“那种认为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地位不重要的认识,也是很糊涂的。”
段子四:某年考研,一考生考场铩羽,失望之余提笔曰“旺旺、老贺、苏力(注:皆法理学名师),今年我不行了,别了!”先生览卷感慨,评曰“你安心地去吧,会有人继续你未竟的事业……”
段子五:一力促成法国民法典的诞生的拿破仑不但是军事天才,为人也风流多情。在某次戎马倥偬的间隙,他写信给一位贵妇人说:“虽然很忙碌也很疲惫,但我一有时间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谁呢?不告诉你……”
在阵阵欢笑声中,我们下课休息,可能是我神往的样子过于幼稚了吧,我旁边的女孩笑道:“看你就是第一次听周老师的课吧?我可是第三回听到拿破仑的情书了!”
女孩一身浅灰色暗花的套裙,头发烫成大波浪潇洒地披在肩上,眉目间很有些飞扬的意思,只是嘴唇偏薄,紧紧地抿着,显得有点凌厉了。
我有些惊讶,我虽然听说过考P大法学院的人中不乏有连年征战的,但没想到这么俯拾皆是。
女孩眼珠一闪,似乎便看出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我只考了一回,去年听了一次学习班,但我还听过他讲的司法考试辅导班,第一次觉得新鲜,听多了也不过那些东西罢了。”
我这会儿正迷着周先生,听女孩的口气很有些不屑,便觉得她太刁钻了,心想谁让你听三遍的呢。我不曾想到世事难料,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足足听了五遍周先生的辅导课,前四遍是身临其境,最后一遍是听的录音,听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傻了,第五遍听完之后,再无力发表任何评论,而现在想起法理学来,脑中仍是一片迷茫。
我们攀谈起来,女孩名叫胡曼卉,浙江金华人,去年从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北京一家律所打工,今年1月份才考了一次P大法学院,就差一点儿,所以预备再接再厉。
胡曼卉左边坐着一个圆圆胖胖的男孩,脸上稀稀落落的几颗青春痘,这时也凑上来搭话道:“真巧了,我也姓胡,也是浙江人,不过我今年是第一次考,心里太没底了。”
胡曼卉一听有些兴趣,问男孩是哪个学校的,男孩掩嘴胡卢一笑:“小学校,小学校……”
胡曼卉还欲追问,我以为男孩的学校没有名气,不好意思说,于是请教他的大名。
男孩又掩嘴一笑:“名字不好,名字不好,我单字一个gao,gaogao秋阳嘛,不过我的姓不好,合到一起就不好了……”
男孩说话声音既低,说得又快,语焉不清,加上我和他之间又隔了一个胡曼卉,我只听到“不好”、“不好”、“搞搞”,不知道他究竟在搞什么。只见男孩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斗大的“杲”字,本来容易写得方方正正的这个字在他笔下仿佛被风吹过,柔弱无骨地斜扭着身子。
我忍不住笑道:“这个字虽然不常用,但意思很好呀,好像唐朝有个大臣叫做颜杲卿吧,就是这个字。”
男孩脸上顿时一亮,笑眯眯地正要说什么,胡曼卉道:“这么生僻的字!这是念‘搞’吗?你叫胡——杲?啊……哈哈哈哈!”
我不如胡曼卉反应敏捷,听她拖音拉调地念出“胡杲”二字,才明白过来,也不由地笑起来。那个男孩显然早已经习惯了自己名字的娱乐功用,看到两个姑娘发笑,立刻配合地作沮丧状道:“我们这一辈兄弟名字都有个‘日’字边,而且据说我五行缺木,当年我爸他们查了好一顿字典才弄出这么个字来,唉!真不幸啊!姓胡的就是不好起名字。”
胡曼卉撇撇嘴:“这跟姓胡有什么关系?……不过,你知道我们学校搞商法的那位‘饭加菜’教授吧,跟你这名字简直是异曲同工。”
我知道南大的那位范嘉材教授,我现在学的商法教科书就是那位范教授主编的。事涉师长,我本不想妄加评说,但突然想起一个笑话,忍不住说道:“我们本科的时候上经贸学院的选修课,老师年轻英俊,叫做范徵,他说姓范的可难起名字了,他的名字总算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他去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的时候,听到人家一口一个‘professor 蒸·饭’,心里暗暗叫苦,真是百密一疏,防不胜防啊!以后我们就叫他蒸饭教授了。”
无聊的笑话最容易让人亲密,我们三个笑了一回,顿时感觉气氛融洽了好多。胡杲听说胡曼卉考过一次,不放过打探消息的机会,问道:“你考什么专业?你说去年考了一次,差在哪一门上?”
我原以为胡曼卉不会愿意提起考场失利的事情,可她似乎正等着这个问题重温自己失之毫厘的遗憾,欣然答道:“自然是考国际经济法了,本来民商法我也考虑过,可还是觉得不如国经来得实惠。其实我也挺想去当刑事案子的辩护人的,我原来是我们院里辩论队的三辩呢。今年P大法学院分数线是320,够低的了吧?可是分数压得特别紧,快两千个人考试,也就一百多个过线的,剩下的分数那么低,想调剂别的学校都没戏。我考了331,高了十分呢,可是综合一的题目也太变态了,我竟然没及格,连面试资格都没有。”
我和胡杲听了都肃然起敬,我没想到胡曼卉考得这么好,由衷说道:“真可惜,你第一次考就这么厉害,真了不起。今年好像很多人都是因为单科不及格刷下来了。你明年肯定没问题了。”
胡曼卉点点头,嘴上却说:“那倒不敢说。你是转专业的,别着急,慢慢考吧。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反正考五六年的也大有人在。等我考进去了,一定给你透露一些内部消息。”
这时候听胡杲嘟囔了几句什么,胡曼卉叫道:“原来你是西北政法的啊!那你刚才干嘛还藏着?我们虽然学校强,可是我们法学院还真不一定比得上你们呢!”
胡杲脸上放光,意气风发,声音也提高了一档,说:“这倒是的。几个政法大学里,中国政法这几年招生太滥了,华东政法的教授们都去下海扒分了,西南政法的好老师都跑到北京上海了,中南政法本来就不如我们。倒是我们学校还有几个人耐得住性子做学问,这些年发展得还不错。”
我好生奇怪,看胡杲的样子明明很为自己的学校自豪,可是为什么刚才要支支吾吾的呢?于是问道:“那你刚才还说是小学校……”
胡杲嘻嘻笑道:“比起南大来,我们学校确实很小呀!”
胡曼卉淡淡一笑,我突然明白胡杲刚才的“小学校”和胡曼卉的“分数差一点”一样,是要引人来问的。原来是我糊涂,还以为那是人家的短处,其实没准儿人家还嫌搔不到他们的痒处呢。
突然,一声清脆的琴弦声打破了嘁嘁喳喳的嘈杂声,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给大家唱首歌。”这声音虽低却颇有穿透力,仿佛玉珠一颗一颗地掉进金盘里,琤瑽作响,柔和又不失清朗。我愕然抬头,只见一个背着吉他的男孩子正站在讲台中央。
这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孩。他的身材修长,泛白的牛仔裤勾勒出他瘦韧的腰身和匀称结实的长腿,肩膀很宽但略显得单薄,脸色有些苍白,栗色的长发披在肩头。男孩的相貌清秀,但鼻梁和下巴的线条非常英挺,眼睛很漂亮,却隐隐地露出一股侠气。他大方地站在讲台上,仿佛丛林中的一只美丽的花豹,说不出的从容和优雅。
我不由得呆住了。我的相貌普通,本来对这么帅的男孩是不敢多看的。可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男孩时,我就震惊极了。他也许并非英俊得无与伦比,但他的气质像极了我在心中描绘了很多年的主人公——一位唐代的将军。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写出一个叫做《白马篇》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历尽坎坷的少年,出塞入塞,从游侠儿成长为一代边塞名将。我把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真和美都加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我的笔墨不足以描摹他于万一,所以我永远也写他不出。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我便分析说,我的主人公只不过是周瑜、曹植、兰陵王、狄青和纳兰容若的大杂烩,是女孩子排遣无聊的一个绮丽梦想。但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沉迷其中。而今天这个素昧平生的男孩一下子狠狠地撞在了我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我又惊又喜,又有些被侵犯了的不安感,很想移开视线,却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看。
男孩轻轻拨了拨琴弦,说:“这是我写的一首歌,叫做《边缘》。”
我在大一的时候学过一阵子吉他,用的是最普通的红棉吉他,只因为学吉他买琴和报班的成本都最低。我学得很差,但有机会听过很多校园歌手的弹唱,觉得大多旋律单调,内容苍白,渐渐也就失了兴趣,开始仰慕古筝和琵琶。可是今天当淙淙的琴声从男孩修长的指下淌出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吉他其实是相当有潜力的乐器,我只是没遇到真正会弹的老师而已。
男孩的声音有一点像许巍,但没有许巍那么沧桑,低沉中还带着年少的清扬:
“那天我为你弹断了琴弦,
从此一个人坠入边缘。
人群的边缘,黑夜里的孤单,
匆匆来去的人们,漠然的脸。
做客京城的这个冬天,
只有风卷尘沙经过我的门前。
……”
舒缓的琴声渐渐地变得激昂起来:
“我身在人群的边缘,
心常飞越华山之巅,
江湖路远,寒山笼烟,
男儿何妨匹马伴青衫。
莫辜负了腰间三尺剑,
何必管明月照向谁边,
了结了今生的心愿。
……”
男孩的吐字非常清晰,歌词一句接一句地撞进我的耳中,我越来越吃惊。如果说前半首歌说的是现代青年人的孤独,那么后半首歌简直就像是武侠片的主题曲了,而旋律上也是前半低沉,后半慷慨。前后两半在词和曲似乎都有些不协调,但男孩缓缓唱来,并不给人突兀之感,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而且男孩所要表达的氛围已经呼之欲出,我俯身写下他的歌词,竟有一种激荡之感。
曲声渐歇,男孩徐徐把琴收起来,一边说道:“如果大家觉得我唱得还可以,可以送给我一块钱,也不必多给,一块钱就行了。”
教室里又响起了嘁嘁嚓嚓的声音,大家不知道在议论些什么,一些人已经开始翻书包找钱了。歌手收钱是很正常的,可是这句话出自这个男孩的口中,令我感到十分意外。从今天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男孩起,我就被他深深地吸引,等我听到他的歌,更觉得似曾相识,但他的歌和气质都透着一股冷傲,虽然让人神往,却很难亲近。这样潇洒的人物谈及钱字,让人不免有些尴尬。
胡杲手里托着两个一块钱的钢蹦,站在座位上,笑嘻嘻地问我们“你有吗?……你有吗?”,我拿出一块钱放在他手中,胡杲看看胡曼卉,指指手里的一个钢蹦说“这个算你的吧!”,胡曼卉撇撇嘴,没有作声。
胡杲又张罗了一会儿,手里握了一把钱,摇摇摆摆地朝讲台走去。送钱过去的人还真不少,粗粗看一下,少说有二三十个,其中不少是像胡杲这样握了一把钱的,可见男孩这首歌唱下来,成果还是让人欣慰的。
这期间男孩一直默默地站着,我没好意思怎么看他,但感觉出他的神色并不太自然,他似乎竭力表现出若无其事或者漫不经心,但有点僵硬的姿势泄露了他的羞涩和紧张。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男孩合上琴套的拉链,大大方方地道了一句“谢谢大家”,背上琴飘然而去。
这是我听到的歌手曹溪的第一首歌,这首歌虽然将我深深地打动,但是它似乎不具备流行的要素,说它古雅也好,说它晦涩也好,反正当数年之后曹溪的歌声传遍大街小巷、他的忧郁与高傲成为少女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的时候,这首《边缘》却永远地湮没在了岁月之中。我曾经找遍了曹溪的每一张专辑,但从未再见过这首歌,仿佛我在2001年夏天的这个上午的所见所闻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但我喜爱这首歌,这么多年来对它一直念念不忘,我常常想,当年听过《边缘》的同学们,是否也会有人在默默地怀念它呢?而我在P大法学院考研辅导班的第一天所听到的《边缘》,似乎竟成了我接下来五年生活的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