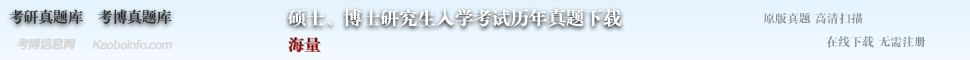|
回首考研来时路:一个中专修机工的两次革命
作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 护泉
但我现在更欣赏的还是当时年少轻狂的我,一个经常望着上铺床板心思重/今夜难得有好梦/因笑一日苦匆匆/闲来倒把雨声听的中专毕业修机工的前瞻和果敢。我要成为研究生,燃烧起这个梦想并不堪此梦的折磨,终于辞职寻梦而去,并为此梦消得人憔悴。为这份自信与执著,至今我万分庆幸,万分激动。
这么多年live to learn,而不知道how to live,有点虚脱,有点垮,开始明白原来这么多年考研一直在支撑着我的躯体。在一种难以摆脱的强弩之末的感觉中最终品味出还是要go on,那就come on。
狮子座的我天生就要不断奔跑,以追得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如果说考研究生是我身为一名修机工时最杰出的策划,那么现在俨然已为人师的我又可以如何?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考博。
老感觉自己过得不如意。昨天我刚摔过键盘,听着翻译公司一遍一遍催命般要稿的电话声,面对因风扇坏掉而CPU发烧的白痴电脑发火,像往常一样起誓再不干翻译。事实上这些天我烦恼已经累积太多:建筑工人阿杜能挣那么多钱,自己买房还要借钱;要考什么教师资格证,不及格还不能评讲师;见过n个女孩,自我评价受挫n次;还有那可防可治但可怕的非典,说是已经under control,还是心有余悸,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出校门……
可是别人说你已经很好了。翻译公司放心找你是因为你终于熬成了名牌大学教师,并有几手三脚猫功夫,父母因为你这个曾经的败家子在茂陵脚下一个有近万人的村落里过日子有了底气也有了盼头,一节课五十大块,你不想上,在西安想上的人走后门都有人插队,想想你下岗的中专同学开蹦蹦车一天才挣多少钱,还好人家女孩能看上你,你才29,可三十多的大龄未婚青年在教师公寓到处都是……
仅从这些世俗指标来看,就能不费力地说明自己的确是考研的大受益者。不夸张地讲,考研对我是鲤鱼跳龙门式的超越,使我有机会在高校工作。但我现在更欣赏的还是当时年少轻狂的我,一个经常望着上铺床板心思重/今夜难得有好梦/因笑一日苦匆匆/闲来倒把雨声听的中专毕业修机工的前瞻和果敢。我要成为研究生,燃烧起这个梦想并不堪此梦的折磨,终于辞职寻梦而去,并为此梦消得人憔悴。为这份自信与执著,至今我万分庆幸,万分激动。
回到1988年中专生动辄就被母校请回做报告的时代,母亲因为有舅舅不上中师最后考中北大的先例极力赞成我上高中,然而保守的父亲在保守的乡亲中调查的结果是送了我一句你想上高中看谁供你的话。在咸阳的纺织中专读书期间,我大致是一门心思钻研象棋,然后,1992年夏进毛纺厂后,就干脆钻到织布机下。满头毛花满身机油手里拿着扳手的我开始想自己要发财,结果在家里搞药材种植受骗,养蝎子害得邻居挨蜇,贩鸡蛋又被洗钱。几年的折腾我真的累了,一屁股沉在凳子上疲惫的眼神落在一张满是油印的《陕西工人报》上,而正是那张报纸的一则招生广告让我过剩的精力有了正确的方向。长期不忿的最后我决意辞职。一年前辞过一次不幸被组织科的人劝回,当时的感觉是进组织科后就不想辞,然而回到宿舍又怎么也想不出呆在这个年年全员销售的国企自己有什么出路,这一次我干脆把我无法忍受这种每月等待工资的生活的辞职报告交给同学,自己直接坐了火车到北京流浪月余,转了北大、北航和人大后,我心想,你总该开除我了吧!
遭遇小偷之后仍活着回来的我给父母这样分析:第一条路,回厂上班,这不可能,厂里多半已经将我开除,就是没开除,我也没脸回厂,免得让人笑死我;第二条路,去深圳打工,我又能找到什么工作?第三条路,给我钱做生意,你们又不放心;第四条路,跟你们种地,你们面子上过不去。那么只有第五条路,给我钱,我要上学。
精打细算的父亲又作了一番调查之后对我讲:大学生一大把,上了又能怎么样?不过你要上,可以,给你钱,但你必须写保证书,你结婚时,不能要家里一分钱,就等于是把结婚的钱给你用作学费了。
我完全同意,但母亲说写什么写,就这样我到了西安。
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坐到书桌前的我觉得念书其实是最轻松愉快的事。很快我就摸出了外语学习的规律。那时在外院有各种各样针对自考生的班,每学期开始我就跑这跑那了解情况,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交叉报班,有接近四学期的时间每周上课达到36课时左右。平时路上都尽量戴耳机练听力,和同学合租的房子墙壁上也贴着好多单词。周末一度从早到晚都泡在师大英语角,碰到生词一句Excuse me掏出辞典就查。有时晚上睡觉做梦也在说英语。暑假寒假照样学习很少间断。外教说我You just want to be special,事实是我真是懒得去管的一头卷曲的长发挺显眼超前加之我学习刻苦,同学有叫我Shakespeare的;好几位女同学问我是不是在背词典,因为她们觉得我词汇量挺大,上课有时给老师递词;父亲来,给他看过拿到的大专证说自己一定要考研,他说这证有用没用?又说学就要好好学,听你邻居房客说都把你叫教授呢,又让我把散放在地上的书好好保管,说以后靠这东西吃饭哩。那时的我不解风情。一个女同学曾对我说,考研的不是工作太差就是人长得找不到对象,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考研?
两年多疯狂的英语学习生活让我提高飞快。自考几乎考一门过一门,综合考试陕西第一,去看分数时有个女同学站在我前面抄我的分数作比较,自己心里偷着乐。由于安排得当,到1998年元月我就拿到了本科毕业证,而且参加了外院的研究生考试。
备考前跟风上了外院的辅导班,又去交大宪梓堂占座上任汝芬的政治强化班,感觉条理清楚了一些,然而,收获最大的却是看到那么乌压压的一片人头,觉得这么多人都考呀,自己一定得拼命。九月份开始,每天早晨在师大图书馆前背政治和日语,忽然有一天感到地面摇晃,就看到很多学生从图书馆里涌出来,斯为那次西安地震恐慌之始。我们就在那个据说是抗六级地震的外院礼堂考试,并且,那一天下雪很厚,我还穿着新买的皮鞋,拿着红牛饮料,准考证是一号。对了,头一天晚上还去过理发店,让人好好揉了揉业已发麻的大脑。
发现综合卷中有些英美文学试题我没有复习到,比如有一道大概是问Waiting for Godot中Godot为什么最后一直没有出现?我就凭想像Godot肯定是那种等你等到心痛但老等不到的那种好东西,籍此发挥八九不离十。
以已经获胜的姿态笑谈考研莫过于此。春节稍稍放松就开始绷紧了弦打探。别人转述的大人物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总要分析半天揣摩半天。风声鹤唳地挨到官方分数发布,终于知道考了第四,我的乐观找到了依据,但是忘了那一年可是我的本命年。
那次复试前就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空气,好像我的复试资格都来之不易。那个无比诡异的五月在我给研究生部打过一个电话后天空开始发黑。电话里说我的口语不行,我想说我实在冤枉,真后悔为什么不在复试时拿录音机现场录音,以便和他们对质公堂?
不记得当时挂上电话的样子了,时间过去太久了。心被掏空了地痛,现在还能感觉到。
或许是因为有考生写了匿名信告发我说我知道考题;或许因为我填的学历只是大专学得太快令人不放心;或许是因为我有点骄傲还不理发。这里面恩怨过节我不想去深究,太伤脑筋。现在,事过境迁,有人走了,有人退了,过去了,就过去吧。
在杨家村的出租屋连续几周狠听贝多芬的命运听得我泪流满面,吃不下饭就买来成箱的酸奶,醒了就喝,喝了就望天花板,用毛笔写了一定要考上北外同声传译的大幅标语贴在墙上,以后就整天到村里村外四处找摊儿,疯了般当头炮反宫马。记得曾经和一个夜灯下头顶闪亮的老头连续鏖战,听他说是某县棋协主席来西安看望上自考的女儿。记得曾指点说一个骄傲村民走的那步是臭棋,结果差点打架,后来,还吃过他卖的豆腐脑。记得棋摊旁边是餐馆,餐馆对面有个房客吃饭老欠帐,女老板叫派出所的人来把他架到车里拉走。记得女老板是个能人,一次吃饭看见她牵线介绍一个幽怨的女孩进一个什么乐队。还有,曾经有男同学和他的女朋友来找我,看我如此沦落在棋摊边站了一会就走了;一个后来听说分进派出所的外院同学找我给他写毕业论文,我回绝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在我那仙人掌都死了的房子坐了一下离去了;我还托朋友拿了我的八字找他的朋友问过我去何方发展方为上策。这么多年live to learn,而不知道how to live,有点虚脱,有点垮,开始明白原来这么多年考研一直在支撑着我的躯体。在一种难以摆脱的强弩之末的感觉中最终品味出,还是要go on,那就come on。
在蹦蹦车的颠簸中离开了我的村落,将听惯了的台球撞击声抛在脑后,宣告自考结束我教书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变得多彩,一切似乎已经看开。就要二次革命了,一点不紧张,基本没复习,只在考政治前背了一个小时任汝芬时政,注意答题字迹工整,竟考到84。考日语时干脆还睡了一觉,那个后来经常可以在校园见到的女监考竟然不忍心打扰。就这么简单。复试我成了第一,谢谢那位已经退休了的系主任对我能刮目相看。
成为研究生的快乐不会持续很长,尽管这一变化substantially改变了我的生活。起初一切都那么光鲜耀眼,树木、餐厅、同学,包括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已经是研究生了,你已经成了研究生了的我。往后一切如常,这样的提醒不再使自己振奋,研究生开始有研究生的烦恼,正如现在的我有我现在的烦恼。翻译可能还要干,风扇还是要换,女孩的面还是要见。
支离破碎地放映这些如烟陈年旧事,倒是帮我强化了对自己的认识,狮子座的我天生就要不断奔跑,以追得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如果说考研究生是我身为一名修机工时最杰出的策划,那么现在俨然已为人师的我又可以如何?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考博,干脆现在就开始看书,看几页是几页,尽管扭头看见窗外,天色已经发白,真是写了一夜。(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99级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西安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