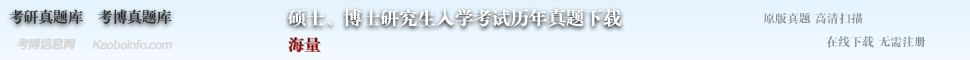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职和辞职考研的伟大考生!
毕业那年的7月2日,在南京市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挤上了回家的大客车。来送我的几个同学已经回去了,过不了几个小时,他们也都会踏上属于自己的漫漫征途。我知道,当这辆车启动以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就将从此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遥远的过去了。
“四年了,……真他吗的像一场梦啊。”我一边凝视着窗外不断倒退的树木和农田,一边喃喃自语。
人类所最害怕面对的,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自己阴暗的过去。即使在今天,我也很不情愿去回想,大学四年本科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经历。如果我回想了,我的大脑甚至会为了自我保护的需要,自动去切断那些不愉快的记忆的线索,以免被那种强烈的负面心理体验所击垮。
幼年时,父母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使我从此生活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学习环境中。虽然中学时的成绩还算马马虎虎,但是却造成了永久性的心理缺陷和学习能力的不完善。高考三天超水平的发挥,让我有机会进入这所还算可以的大学,读一个据老师说是很有前途的专业。兴奋的父母邀请了县城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在最好的饭店里摆了几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其实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并没有多少钱的。
进入大学以后,不堪回首的历程就开始了。美好的希望,很快就被对学习方式的不适应所造成的力不从心粉碎了。第一个学期,数学就不幸挂了红灯。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课堂上我完全无法跟上老师那一节课十几页的节奏,以至于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几乎什么也没学会。当考试结束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望着空空如也的答卷,想起母亲劳累而憔悴的面容,不禁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第二学期,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为了赶时髦,号召大家集资购买了一台电脑。虽然是486兼容机,但是在当时还是花了整整8000多大元。经历了学业上的严重打击后,我疯狂地爱上了这台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的机器。与此同时,也爱上了陪伴她到来的那个最最可怕的魔鬼。凡是我不喜欢的课程,我全部都会逃掉,在宿舍里与她做伴。期末,数学再一次挂红灯,别的科目勉强及格。这完全是活该,我清楚,因为直到考数学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那个虚幻的剑与魔法的世界中麻醉自己。而当时我连什么是全微分都不知道。
在后面的几年里,我越堕越深,红灯也接连不断。我的表现让父母伤透了心,但是看着我颓废的样子,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也无可奈何。同学们也开始看不起我,这让我愈加只能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找胜利和征服的快感。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度过了失败的四年。唯一的收获就是,电脑知识和水平大大提高,但是也还属于不值一提的那种。直到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能力通过计算机水平考试的三级,也写不出一个像样的C语言程序。
大四的时候那次考研纯属自欺欺人,因为我根本就连一分钟也没有复习。象征性地考了一门英语,然后我就溜出去找工作了。这此努力给我带来的回报是,我总算寻到了一家愿意接纳我的公司。毕业前的几个月是最后的疯狂,我和别的堕落者们整天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电脑机房里,机械地移动和点击着手中的鼠标,就像一具受邪恶魔法控制了的僵尸。
当勤奋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生活用品搬进研究生宿舍的时候,我只能提着所有的行李,灰溜溜地朝老家的方向滚蛋。汽车行进在颠簸的公路上,我注视着自己脚下的两个大箱子,是那台早已过时得没有人愿意要的486电脑的显示器和主机。这,难道就是我在大学里的全部收获?讽刺。极大的讽刺。
故乡的小城依然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宁静和喧嚣。父母永远不会真正责怪孩子,但是从他们的眼睛里,我分明看到了伤心的神情,失望的目光,刺得我的心一阵阵收缩。
“我说老吴啊,你们家小浩子毕业分配到什么单位了啊?”邻居毛大婶串门来了。
“在浙江,一个制药厂。”母亲满脸堆笑地回答。
“啊,怎么分配那么远啊?”又是一个计划经济模式的问题。
“现在哪还有什么国家分配啊,工作都是自己找的。”母亲不紧不慢地做了符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回答。
“哦,我听说大学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呢,你们家浩子有没有考啊?”
这种尴尬的问题!我坐在一边,感觉犹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都不舒服起来。但是我又不能走开,那样很不礼貌。还是硬着头皮听下去吧。
“唉,他上学上够了,想工作了呗,能怎么办。”母亲的口气一转。
我再也忍不住了,借口上茅厕就跑开了。我在厕所里用头使劲撞击着墙壁,希望自己能够忘掉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可能吗?
短短的40天过的很快,就要去那个远隔千里的单位报到了。母亲执意要送我过去,我虽然强烈反对,指出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等等,但是终究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8月12日,我和母亲一起,踏上了南下的路途。
到了这家号称全国资产价值排名前十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城市,才发现它其实比我所来自的县城并大不了多少。由于在海边的缘故,空气中弥漫着咸的味道,让我这个内陆地区来的人好不适应。街道不大但是很繁华,到处是店铺和大减价的告示,洋溢着一片商品经济的气息。
由于宿舍紧张的缘故,公司把我们这届的大学生临时安排到港口旁边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母亲回去了,晚上无事的时候就看看电视,翻翻书。白天在厂里,看到那些高耸的发酵设备和散发着怪异气味的管道,虽然有一点新鲜和好奇,但是总觉得那不是属于自己的,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东西。
颇有意思的是,公司的第一个培训项目竟然是为期两周的军训。这里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地方,距离台海前线比较近,部队营地非常多。我们厂和驻军某部炮兵二连是邻居,经常在工作的时候听到沉闷的迫击炮声。一群文弱的大学生们就在那里练了半个月。这是当地所有单位的传统。
第一个月是在车间实习,三班倒。车间里的操作工大多是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女性,她们对我这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感到很好奇,经常主动找我说话。我渐渐了解了这里的一些情况:这家企业是从9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生产西药原料,目前效益还算比较好。至于什么前途和理想之类的,她们大多都不愿意去想,认为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安静的生活,就很满意了。同时,单位还有一部分职工就是当地的农民,因为占用了他们的土地建造厂房,根据政策规定,必须把他们招进企业,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名额是每亩耕地2人。这些工人们虽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却丝毫不比技术人员低。大学生们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往往都很不满,我却觉得无所谓,因为国有企业里这种事情简直司空见惯。唯一让人不舒服的是,他们在食堂里排队打饭的时候经常粗鲁地挤到队伍的前面,以至于当我终于老老实实的等到窗口前时,面对的只是一大堆空的菜盆和一些残羹冷炙。
实习期结束后,分到了车间的菌种实验室。因为岗位的重要性和对技术的较高要求,单位对这一届的大专学生进行了集中讲课和实验技能培训,并且最后还要考核。由于在本科期间养成的对考试的恐惧心理,而且专业也不如别的毕业生对口,所以我如临大敌地仔细准备了好几天。结果就不用说了,开卷考试,无人监考,题目极端简单。“原来考试也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我带头交卷的时候困惑地想。
晚上回到宿舍后的时间如何打发,确实是一个问题。和我同房间的是一个浙大的和一个南京化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学化工专业,工作地点距我所在的车间很远,只有回宿舍以后才能见到他们。他们往往会看电视到深夜,而我觉得屏幕上的那些穿着清朝服装打架斗殴或者谈情说爱的男女们实在是很无聊。于是我就开始和大学的同学通信。有一个和我最谈的来的同学,我每次给他写信都会有厚厚的六七页,直到11月底他要专心复习考研而不再继续联系。
然后我就认识了小张。他是和我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但是是硕士生,所以住宿条件就要好一些。进入他的房间,首先见到的就是一台崭新的电脑和大量的盗版光盘。“原来也是个电脑爱好者。”我心中窃喜。从那以后,我在晚上和双休日就经常跑到他那里去蹭机器。他虽然一定不太高兴,但是也没说什么。
秋天很快过去了,海滨小城刮起了凛冽的北风。工作一如既往的平淡,心中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母亲在送我来的路上曾经说:“到了那边,可能就会永远在那里了。”难道这句话正在变成现实?
过年了。和所有的单位一样,我也领到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年货,提着大包小包回家去了。再次回到单位后不久,我就接到了通知,调我到厂部菌种室去工作。于是我就来到了这个净化程度很高、比车间的条件好得多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全部是大学或大专学历,多为本地人,年轻漂亮的MM占绝对优势。实验室的组长是一个从安徽某企业调过来的中年男人,个子一米八高,在相对矮小的浙江人中间鹤立鸡群。他很好心,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令我十分感动。每天的工作依旧平淡,唯一的乐趣仍然是隔三差五地跑到小张那边去蹭机器。
有一天,实验室里又来了一个年轻人小丁。他也是从下面车间调来的大学生。让人好奇的是,和别人抽屉里的化妆品或者报纸杂志不同,他拿了很多大学教科书过来。每天中午,别人回家或者就在实验室里休息的时候,他独自拿出一本英语词汇书,就开始默默地背诵。我渐渐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兴趣。
“他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了。”组长和我说。“他去年考上了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研究生,9月份就要去报到了。在这边工作就是为了再挣几个月钱。”忽然间,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念头在我心中涌动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一次来到小张那边蹭机器。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叫住我,和我谈了几句话。
“小陈,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他说。
我没有说话。
“以你的情况,完全应该去进行进一步的深造。你还年轻,在这种地方呆下去……,太浪费了。”
“我正在考虑。”我回答。
“不要考虑了。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如果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不觉得可惜吗?小蔡他们你也看到了,也是本科生。干了三年了,不还是在车间里做实验?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也不会巴结他们,没机会得到重用的。
“我打算报考MBA。”小张继续讲,“不会是今年,因为工作年限不够。但是我一定会尽快的。你看我们许副总,也是和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就因为在美国读了硕士,回来就拿50万年薪。你要是真想有些作为的话,以后就该少来这里玩,多学些有用的东西,对不对?”
“……”
回到自己的宿舍,我思考了很久。是呀,我们年纪还轻得很,怎么可以如此不思进取,自甘沉沦!这里的环境,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喜欢。以前住的招待所,楼下的巷子就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大批服装妖艳的夜莺们公然和客人当街谈价,每天晚上的成交量据说达到500多人次。外来的打工者很多很杂,时常发生治安案件。城市里没有高等学府,人们的头脑中都充斥着金钱至上的观念,暴发户比比皆是,自命清高但是收入菲薄的学生在他们看来是那样的卑微和不值一提。老总在一次会议上一句有口无心的话“大学生我招多少有多少”更是让人士气低落,备感压抑。
我抬起头,看了看自己的房间。白色的墙壁所围成的50平方米的空间里,平行摆着4张铁床和被褥。没有桌子和别的家具,只有几个用来装土霉素的大木桶底朝上放置着,铺上报纸充当凳子。整个屋子看起来就像一个阴森的太平间,只有壁橱里摆放的简单的生活用品显示着一点活人的气息。我本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但是精神上的贫乏是最最令人感到恐惧的,这种感觉会让你颤抖,让你窒息,让你完全无路可逃。
“不行!我要学习!!!~~~~”我忍不住高声喊叫起来。叫声伴随着后面的阵阵狂笑,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回荡着,余音绕梁,经久不息。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学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非常肯定,我是再也不可能重新去学原来的专业了。我在这个领域里已经伤痕累累,筋疲力尽。大量失败的、消极的体验使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决心永远告别这个让我伤透了心的学科,寻找一段全新的事业。
确定新的努力方向并不难。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我了解的比较多的,也比较喜欢学的,就只有计算机科学了。虽然我的基础并不好,数学也一塌糊涂,但是一旦你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不是出于赶时髦去学,任何困难就都不能称为困难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下定报考研究生的决心,而是打算先考个证书,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于是,我把一些基础的计算机教材比如《离散数学》和《数据结构》,还有一本计算机应用技术考试的辅导书,请进了实验室。然后,每天中午,以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便如饥似渴的埋头于这些知识的海洋中。
这些教材毫无疑问不是好啃的骨头,但是我并不是太着急,因为我知道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打好基础。概念看不懂?不管它,下次再说。不久,《组成原理》和《操作系统》也被我带了过来。为了掌握一点应用能力,我还根据别的计算机电脑爱好者的建议,学起了Visual Basic。我仍然经常跑到小张那边去蹭机,但是主要的上机内容变成了调试程序。由于我自学过C语言,所以学起来还不算吃力。然而我并没有深入去学这些开发工具,因为4、5月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提前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即当年考研。
原来,我这一届进来的大中专学生共有150多人,其中本科就有50人以上。大多数人的想法其实和我大同小异,那就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耗尽自己的青春和激情。于是,从9月份开始,就有个别找到了更好门路的毕业生陆续向上面提交辞职报告。一开始管理层根本不把一两个人的离开当一回事,但是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使余下的人心理产生了波动。紧接着,住宿环境的恶劣,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辞职走人的念头。由于工作合同里规定,工作的第一年,合同双方都可以终止劳动合同而不负担违约责任,因此,到春天的时候,越来越多呆不下去的毕业生开始提出辞职,渐渐的形成了一股挡不住的潮流,每星期人力资源部都会收到一到两封辞职报告。而每一个人的离开又给剩下的人更大的震动。这种多米诺骨牌现象使短短的两个月内,本科生仅剩下不到一半。
“无聊啊,无聊!”我用一种装酷的语气对同宿舍的浙大毕业生小彭说。“没有酒,没有性,也没有流行音乐。生活是多么的无聊。”
小彭没有理我,抱起一本《有机化学》就开始啃起来。他已经决定考研了。
我自觉无趣,也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
工作并非完全没有意思。我们公司和一家保加利亚公司的技术转让合同正在生效,对方派了三名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实验室指导这个项目。一同进驻实验室的还有厂部办公室的一位漂亮MM小唐。她是中国药大的毕业生,和我同届,因为英语好,一直担当文件翻译的任务,现在被派过来负责外籍技术人员和我们之间的交流工作。三个外国人中,最常过来的是一个叫娜佳的女工程师;不幸的是,她的英语口语也是最差的,充满了生硬的斯拉夫味道。可怜的小唐常常要对方重复几次后,才能分辨出那些僵硬的音节。
小唐不在的时候,就只能由我来充当翻译了。因为别的技术人员完全无法听懂除了Yes和No以外的任何单词。帮助她们交流无疑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但是多少对我的英语会有点好处。毕竟,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5月的一天中午,当别人都走后,小唐坐到我旁边。
“我觉得公司真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她说。
“白天8小时内的工作就不说了,而且根本做不完。还要我们带回去做。经常要做到晚上9点钟。
“加班费?没有的事。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不做反而是不正常。
“这两个月到你们实验室来做翻译还好一点,可是你知道吗?来了大半年了,我现在的存款只有600块。科室的工资比不上你们实验室高,而且我们女孩子的花费也比你们大。
“唉,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她红着眼圈,絮絮叨叨地讲。我一边听,一边考虑着自己的出路。
“我觉得干这一行太危险了,你不觉得吗?”她继续讲,“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就因为用实验室的微波炉做夜宵吃,就得了癌症。
“那个微波炉平时是用来加热化学药品的,都是像亚硝基胍这样的致癌物。
“鼻咽癌。上个月已经死掉了。导师赔偿了他父母10万元。”
看了看桌子上的瓶瓶罐罐,我感到后背有点发凉,鼻子仿佛也不舒服起来。
“很多人都走了。我们学校小曹上星期也走了。
“你要是想走,最好8月份以前走。以后走的话,就要付4000元违约金。
“你问我想不想走?哎,我是没办法了。你们还有技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儿,我还能去什么地方?哪儿愿意要我?”她絮絮叨叨地说完,出去了。
辞职的人数仍然在增加。而这时又传来小道消息,研究生的公费还有最后一年。以后就全部都是自费了。我最终做出决定,今年拼一把!
每天中午的实验室里,所有的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是愤怒的大学生,手中捧着英语、政治等各种各样的书本,眼睛瞪得大大的,恨不得一口把书吞到肚子里去。另一派则在另一个房间里,身上披着毯子,安然享受甜蜜的午睡。前一类全是男性,后一类全是女性。
当毕业生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时候,管理层对如此惊人的人才流失现象再也无法漠视不管。6月中旬,许副总亲自召集所有当年进来的大学生开会,讨论“如何更好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我们在会上被要求回答一份显然是从国外公司翻译过来的问卷,然后就开始自由的讨论。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大学生们无所顾忌地说出了自己之所以不满意的原因,包括嫌工作没意思,对前途感到渺茫,收入低,住宿条件差、宿舍里发现有做试验用的小白鼠在跑等等。然而限于企业的国有性质,管理层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答应在某些程度上进行改善。双方的语言渐渐激烈起来。管理层搬出了一个埋头工作5年终于成为主任级骨干的人来做我们的榜样。浮躁的、听说过太多快速成功故事的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屑一顾。最后,一个大学生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我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了十几年书,还不如农民工家里的五分地!”
“这是什么话!”老总被激怒了。“你管人家的地干什么?农民工就能不是人才吗?农民工只要踏实肯学,我看未必不如大学生有前途!”
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不敢喘气,愣愣地望着面露愠色的老总。
“大家别这样,别这样啊。”许副总出来打圆场了,“哎,小陈,你还没说话呢,你说说,现在这么多人辞职,你有什么看法?”他向自己的校友招呼道。记得他来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坐在那里一个劲的说英语,一个汉字也不说,吓走了不少人。我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和他顺利对话的毕业生之一,而且是同样的专业,所以他对我的印象比较深。
“哦,我觉得这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谈不上谁对谁错。”我故作憨厚地回答。
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啊呀呀,今后该做些什么呢?”我在宿舍里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
“完了,你也要走了。”南化的小孙转过头来看着我,“哎,人,又少了一个!”
人心已经处于溃散的状态。6月24日,我利用双休日再加上请了一天假,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母校。物是人非,除了几个读研的同学,我再也找不到认识的人了。幸好我在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还有一个老乡,读研一。在她向我推荐了一些复习参考书后,我把身上的盘缠一笔一笔地换成了陈文灯,林代昭,还有王长喜。回到单位后,我把大部分的上班时间贡献给了那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复习指南。同事们知道我是肯定留不下了,所以也只能默许这种事情的发生。
“如果你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我记不得这是谁的名言了,我只知道我必须为自己的过去还债,必须把以前逃掉的所有数学课全部连本带利地补回来。这是宿命吗?我不知道。以前极端憎恨的那些蝌蚪般的数学符号在我眼里仿佛变得可爱了。原来数学是那样的精巧,那样的奥妙无穷,那样的引人入胜。她充满了逻辑,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美。我认真琢磨每一道题目,认真阅读每一条公式,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复习得越深,越为自己以前对它的轻慢和不恭而感到羞愧。
晚上的时间是用来复习英语的。我一边背单词,一边做阅读理解。同样令我羞惭万分的是,一向自诩英语不赖的我,竟然会有那么多不认识的词汇,那么多看不懂的句子。感到自己是一只井底之蛙,我只有虚心学习学习再学习。
以前在学校里被我认为是离自己最远、最不可能学好的政治,忽然间也变得那样的可爱。我不仅仅在背它,我在用我的全部身心去思考它,去理解它。我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我叹服于马哲的高深,我叹服于政经的博大,我叹服于毛概的朴素,我叹服于邓论的扎实。在无数伟人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之墙前面,我只能象一个小学生那样低下自己的头颅。
7月初,我终于也递交了辞职报告。老总在从我手中接过那个薄薄的信封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丝惊讶的神情。他已经完全麻木了。“去人力资源部开一个单子,照着单子上的要求去各部门办理手续。最后去区劳动局把档案拿出来。”他机械地背着台词。
各部门办理手续的速度也快的出乎我的意料。看来他们都是轻车熟路了。
我正式离开的日子是8月5日,离我来单位报到相距359天。
因为存折不能跨省存取,我取出了我一年来的所有积蓄,共计7650元人民币。这,就将是我下半年考研的全部经费了。
我打好了行李,微笑着和同事们告别。组长来了,他送给我一支派克钢笔作为临别的礼物,我从他的眼神里能读懂这件礼物的深刻含义。小彭也来了。小彭也交了辞职报告,几天后也要走了。
客观的说,这不算是一个很差的单位。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感到并不好受,感情上仿佛欠了公司一笔债。如果我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尽力报答它对我一年来的收留之恩。
回家的车启动了。这个留下了我一年美好青春,留下了我欢笑和汗水,留下了我成长和成熟的脚步,留下了我一段永远抹不掉的回忆的海滨小城,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忘不掉,那满街充满了南方味道的浙江口音。忘不掉,那些热心质朴的同事和领导。忘不掉,那夏日夜晚阵阵凉爽的海风。忘不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当客车里播放起李宗胜悲壮的歌声:“嘿哟嘿嘿嘿哟嘿,管它山高水也深,嘿哟嘿嘿嘿哟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两行热泪终于从男子汉的眼眶中奔流而下!
“……嘿哟嘿嘿嘿哟嘿,管它山高水又深,嘿哟嘿嘿嘿哟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哟嘿嘿嘿哟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从那天以后,我便彻底恢复了自由,开始了专职的考研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