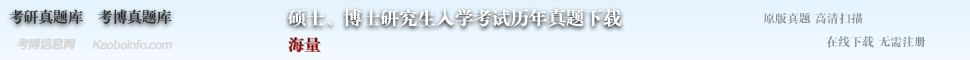清华大学的王垠在还有一年就要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下放弃了学业,经过相关媒体的报道,也引发了新的一轮对于高等教育科研现状和高等人才培养体制的讨论。
以论文衡量学术优劣正成为窒息学术创造力的桎梏
以论文发表在SCI的数量来作为评定学术研究水平能力,这一制度的本意无非是在学术研究中引入一种激励机制,并以一种在形式和程序上的合情合理来进行优胜劣汰。然而当这一制度成为衡量的惟一标准的时候,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最首要的一条就是学术优劣的标准能否用单纯的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而围绕着发表论文这一硬性指标,甚至当科研经费和研究课题的设置都依赖于这一制度体系的时候,研究者如何能发挥其学术创造力从事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一个具有良好设想的激励机制正成为窒息学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桎梏。
一个更能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佐证是,前不久刚刚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的经历带给我们中国数学家的震撼。在怀尔斯决定全力投入到破解费马大定理的研究中后,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的成果,没有任何学术课题参加评估,他只关心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能否解决是一个天大的未知数。然而,他最后拿出的论文恐怕是近300年里数学界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要是在中国现有的学术评定体系和制度下,那么怀尔斯的命运只有一个:没课题,没经费,没工资,离职。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下,出怀尔斯这样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SCI本来是一个好的制度,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把它用滥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学术产出的激励机制肯定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更好的学术产出激励机制呢?
美、英等国同样重视论文的评价功能
SCI的评估制度并不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恰恰是引进西方教育科研发达国家的经验,而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其实在诸如美国、英国等教育科研强国也并未能幸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怀尔斯其实也是一个特例。我们不要忘了怀尔斯是在具有近乎终身教职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就的。或者说,他是在有本钱的情况下承担了巨大的风险,用自己一生的学术生命作了一个赌注。而假如怀尔斯就处在王垠现在的位置上,或者是刚刚获得高校教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讲师,那么恐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或者科研院所会给他提供一个下赌注的本钱。
在学术日益专业化,分工精细化的今天,SCI的评估给学术产出的量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也仅仅是一个参考。然而为什么在中国这一标准执行得如此彻底?当我们在众口一词得责难现行学术环境的急功近利和缺乏理性的同时,在这种大众化真理通过舆论飞速普及的同时,我们是否反思过在背后还有更深的一层制度环境?我们自己是否也想过自己也是促成这一切急功近利和缺乏理性的一分子呢?
王垠若不发表论文,他的学术成果如何量化
当一位博士生导师依据自身所作出的学术判断选择了一位考分不高而舍弃了另一位考分高一些的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普及化真理的众口一词对那位博导的谴责,这正好和我们今天对SCI评估体系的谴责的逻辑是一个背弃,我们对于相同的逻辑选择了不同的“真理”,这一切是偶然的么?学术研究的产出的逻辑很显然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的工业产品的产出机理一般可以通过数据,乃至用分数量化的。然而获得高分当博士和SCI的论文数量获得博士学位难道不是同一个逻辑么?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王垠真的可以在不发表SCI论文,没有可以量化的学术成果(就像考博得高分一样)顺利地拿到了博士文凭,我们难道不会去谴责给他颁发学位的学术评审委员会么?我们不会说背后有“黑幕”和“学术腐败”么?
所以,正是在独立的学术评审制度无法有效建制的情况下,包括匿名评审,乃至学者权威鉴定制度在现有的学术环境下尚不够成熟,甚至无法奏效的情况下,SCI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只有这个制度才提供了一个程序正当的评价合理性的依据。SCI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普及并成为一种近乎惟一被认可的评价标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卸责制度,它使得学术产出评估者和学术产出者都免于承担某些不必要的学术风险,道德风险。毕竟学术的成就是未知的,而风险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甚至后果是严重的。这是一个多方无奈之下的一个迫不得已的制度选择。
要消除这种局面,在现有的学术评估制度和学术环境存在诸多不足的情况下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呼吁独立的学术评审制度和匿名评审制度进一步深入到现有的评估体系中,并使SCI恢复其本身的职能———作为一种辅助性评估手段。
最后一点是,制度永远是为大多数人所制定的,不要忘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从来都不是从制度体系内中产生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在教育制度不再是贵族和精英专利的今天,这种制度是不可能用来培养天才的,也不可能再承担这样的重任。
王垠选择了离开,他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可能他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也会失望,发现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作者:北京编辑 夏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