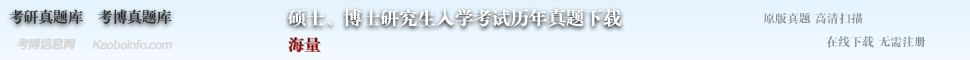新闻背景
雷闯去年获得保研资格,他选择了中科院过程研究所。但身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雷闯获悉,“大三阳”考生没有被录取的可能,于是他开始尝试中科院系统其他研究所,结果31家研究所有26家拒绝了他。为此他着手向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求助,但524封求助信换来的结果仍然令人失望。
2008年11月19日,雷闯在肝胆相照论坛发了一个《号召100所高校大学生就乙肝歧视致信教育部和卫生部长的倡议书》。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的有关规定,雷闯今年8月17日提出了办理从事食品行业健康证的要求,8月21日被拒。医生的解释是:“虽然有法,但是没有上级文件,我们不能办理。”
表示“拿不到健康证,誓不离杭,誓不理发”的雷闯,想方设法找到浙江省卫生厅杨敬厅长,以及浙江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反映情况。到了8月27日,眼看办证无望的雷闯在浙江省卫生厅门口举起牌子:“浙江省卫生厅,你妈妈喊你回家办健康证检查乙肝两对半”,并告知西湖区卫生局,如果不能在9月1日前拿到健康证,将提起行政诉讼。
雷闯最终于9月1日拿到了健康证。
因为“中国第一例乙肝病毒携带者办出健康证”这个身份,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研究生的雷闯,昨天出现在上海交大化学化工专业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课堂上,这个曾经表示不拿到食品卫生类健康证就不剃头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换了“板刷头”。对于在上海交大校园生活的第一天,雷闯心情不错:“在上海交大没有感受到歧视。同宿舍的8名同学早就知道我的情况了,没人对我‘另眼相看’。”他表示,紧张的学业会让他推延在上海申请食品卫生类健康证,但他会一直关注“乙肝歧视”问题。
“是两位妈妈给了我坚持反乙肝歧视的动力”
“从2007年开始反乙肝歧视一直到现在,是两位妈妈给了我动力。一位是我的妈妈,一位是我的浙大校友周一超的妈妈。”雷闯昨天向记者说起反乙肝歧视的原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或者为人父母的,应该能够体会作为母亲在孩子遭受无谓的乙肝歧视时的那种痛苦和无奈。”
让雷闯记忆深刻的事件发生在2007年7月,他的哥哥从长春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道路桥梁专业毕业,成功应聘到一家大型国企。正在举家欢庆时,哥哥被企业告知“大三阳必须转小三阳后才能入职”。此后大半年,几乎雷闯每次往家里打电话,妈妈都会痛苦地自责:为什么要让两个孩子得乙肝,而不是爸爸和妈妈。只有小学文化的妈妈现在还责怪雷闯兄弟当初没有听她的话,吃治乙肝的“土方子”。
雷闯还多次去看望因为遭受乙肝歧视杀人而被判死刑的浙江大学毕业生周一超的妈妈,这位孤独的老人同样深深地打动了雷闯。2003年,浙大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周一超报名参加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政府招收9名乡镇公务员考试,笔试排名第三,面试后总成绩排名第五,却因为体检结果为“小三阳”而判“不合格”。得知另一名手指残疾考生属合格的信息后,遂用水果刀刺死一人、重伤一人。
“每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后面都有一对父母,都有一个家庭,我做这些就是为了不让更多乙肝孩子的妈妈变得像我现在的妈妈,也不想让有乙肝孩子的家庭变成像周妈妈这样的家庭。”雷闯坦言,“其实我觉得接受媒体采访并不能改变现状,但我希望至少媒体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乙肝歧视是不科学的。”
今天和导师“双向选择”
“其实我入学前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乙肝歧视在我过去的经历中太过常见。”雷闯这样告诉记者,“不过入住宿舍和同学交流过后,发现大多数同学对乙肝还是持宽容态度的,可能现在网络发达了,很容易就能够查到乙肝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对日常生活是否有影响。”四室一厅的宿舍要住8名同学,雷闯的同屋是个山西人,“我真佩服你”就是同屋对他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缓解了雷闯最初略有忐忑的心。
据学校有关负责老师介绍,雷闯和他的同学们今天就要与化工学院老师进行双向选择,不过对此雷闯并不太担心。负责雷闯这个年级教务工作的徐老师表示,上海交大招收乙肝学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只要肝功能指标正常,就可以入学。对于雷闯这样的学生,学校将在统一的新生体检后,根据医疗部门对他的身体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医疗部门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学校也绝不会“画蛇添足”,给学生带来无形的压力。
雷闯告诉记者,在他离开浙江大学之前,以往一起跟着他做乙肝科普宣传的学弟学妹们终于完成了他们的一个共同愿望——向学校申请一个开展反对乙肝歧视等等公益科普活动的社团。
推迟在沪申请健康证
在9月2日的博客中,雷闯写道:今晚我将去理发,明天前往上海交大,开始我新的求学生活。到了上海之后,将会继续在上海办理食品工作健康证。不过昨天雷闯却表示:一入学,功课学业扑面而来,不能第一时间完成在上海办理食品工作健康证的计划了。“至少要到下周才能考虑这件事了”。
雷闯说,对于反乙肝歧视,可能不会像假期中那样全身心投入,“但我一定会关注并且参与反乙肝歧视,从长期来看,我希望乙肝歧视在中国不再存在,虽然我知道单靠我的力量肯定不行;而从短期来看,两年半以后,我也面临就业的实际问题,乙肝歧视显然也会影响我和那些和我一样的人。”说到这里,雷闯流露出些许无奈。
本报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