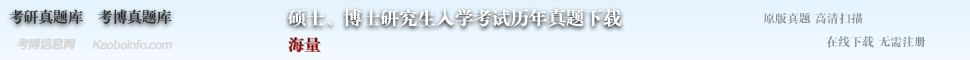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总有一种感情,一种并没有实现自己一生梦想的深深的愧意和淡淡的忧伤。只有那个梦想代表着美好,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我崇尚那些不断进取的灵魂,我羡慕那些走到成功地位的个体,我理解所有为生命的价值而不懈努力的精灵。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很多,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点色彩,没有一点张扬的人生。
有意思的是,1998年的夏天,当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中时,我正在参加县委年轻干部轮训班,轮训班结束时,我就是副科级干部了。但我很快乐地离开了那个许多人想进入的机关,一点留恋都没有的彻底的快乐。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习惯于变动,习惯于去追求一种叫做梦想的东西。检视十年间我离开校园、踏入社会、再回到校园的心路历程,才明白人总是要在不满足中寻找一种心灵的慰籍,而就是这种慰籍驱使着人去做更大的跳跃,更美的飞翔。奋斗与成功,漫漫人生中最让我牵挂的也不过就是这两桩事情。而每一个成功故事的背后,都藏有难于言说的心路历程。十年的光阴倏忽而逝,曾经的梦想在我的记忆里像野兔一样快速地奔跑。
母亲去世时我十六岁,初三刚毕业。父亲要我在跟表哥学手艺与读高中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了后者,生活中艰难的历程便由此拉开了序幕。十九岁那年(1990年)我成为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入江西省抚州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系。穿过高考黑森林,面对突兀于眼前的所谓大学,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惆怅,想着平时在班上排名第二,与第一名的同学不相上下,而第一名的同学考入浙江大学,自己却只能上专科时,就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想到日后将伴我一生的三尺讲台,流水一样来来去去的一茬茬学生,想到青春梦想就此绝版,我觉得世界一片迷茫和混乱。人生就像一群鸟落在树丛里,起飞点都不一样,似乎注定了我要跟在别人后面跑。我很想重读一年高三,圆我的名牌大学梦。但家境的困窘和日渐衰老的父亲的那份满足,使我带着失落上路了。
一年后,一个叫云的女孩进入了我的情感世界。云和我是同乡,相似的家境使我们很快成为知心朋友。那时候我期待着一种淡蓝会接上另外一种淡蓝,而无边的心事正缓缓陷入她睫毛深处那潭幽幽的深水,到了暮春时节一片惊雷过后,俨然已是诗意淋漓,月白风清。云知道我很努力,一直在自学英语,便把她哥哥读大学时用过的英语资料全都拿给我,并对我说:“好好念,毕业后去考研究生。”当时学英语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因为师专的学习实在太轻松,而我又属于那种自命不凡的人,所以学英语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寄托。带着甜蜜的心情憧憬着将来,在与云同学的两年中,是我青春岁月里最为闪亮的一段日子,在那样纯粹的一种想像中,自学英语被赋予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两年后(1993年)的夏天,我师专毕业返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云却只身去了广州闯荡。云说,邂逅是一种伤心的美丽,就像那躲进河流的雨滴,岁月会把签名和留影都遗忘。现实将我所有的想像都击得粉碎,一段感情从心里剥离,身体带着一种厌倦与迷乱行走江湖。云走了之后,我时常想她,想得心痛。朋友劝我说,你怀念的不过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寂寞时想想,暖暖自己罢了。但我知道自己是在沉甸甸地想她,想当初的那份快乐,想像那种以为可以携手到老的黄金岁月里的爱情。我需要找到一种寄托,于是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极富忍耐地行走着,以为那样可以安妥我动荡的灵魂。但这样也无法对自己的命运有所交代。终于剪了长发,终于把云的相片拆下,把荣誉与爱情锁在箱底,收拾情心,开始现实的生活。我渴望在情感中丢失的东西,能在另一种奋斗中找回来。我想起了云曾经给我的那些书,想起了她曾经给予我的那些憧憬,考研--成为我从平凡抵达崇高的惟一途径。任教的乡级中学地处偏远,每天只有一趟中巴车进出,电视接收信号时有时无,冬季缺水时照明供电到晚上八点半便没有了,只有蜡烛与我的梦想一起燃烧。1994年冬天我第一次参加了考研,英语和政治都过了全国公共课分数线,专业课因为没有买到教材,所以总分没上去。但我很满意,毕竟,我只是一个专科生。
1995年冬天我带着疲惫仓促应考。考前两个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到学校考察我,暗示要调我到县委去。于是我在同事们的怂恿下去“走关系”,想脚踏两条船,考不上研究生我也可以离开那个小镇,进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关工作。我分神于那些俗事当中,考研的准备工作被分割成各种松懈的理由。失败是必然的结局。好像是一种补偿,1996年春天我如愿进了县委宣传部,上班第一天部长约见我时就明确告诉我,进来了就别再想考研的事。曾经到学校考察我的副部长给我的忠告是:在机关里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连续两年的失败使我觉得人生无常,像考研那样刻意去做的一件事,结果都难使人遂愿。这时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花开了就会结果,不是所有付出的努力都能抵达成功的彼岸。我为自己寻找了一种安于现状的借口,努力地工作。1996~1997年我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江西日报》等报纸发表了210余篇稿件,还获得1997'年度江西新闻奖(二等),担任了新华社江西分社特约记者、《江西日报》特约通讯员、县委宣传部报道组长等职,在赣南的那个小城颇有点虚名。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生活。
现实的生活令我麻木,没完没了地写材料,没完没了地唯唯诺诺,熬在机关里等提拔。而我像平原上的一个小屋,身后没有大树做风景,看得见的前程,使我--一个农家子弟--麻木得连绝望和痛苦都没有了。1997年的秋天,一位朋友考入厦门大学读研究生,临行前的酒宴使我走到了生活的临界。回想前事种种,一切都好像是一个黑色幽默,只是嘲讽的对象是我自己。考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失败了,再多的煎熬与苦痛都没有人会理解。曾经的青春让我感到心痛,使我的那些故事狼狈不堪。青春不应该在云端上,它属于每一个人,有泪水,有痛苦,有思考,有和现实的碰撞。如今,那种无所适从、头重脚轻、不知坠落何处的命运,想起来令我心寒。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总有一种感情,一种并没有实现自己一生梦想的深深的愧意和淡淡的忧伤。只有那个梦想代表着美好,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有时候,一个梦想的存在,就足以成为人们幸福的基础。
曾经,在一年又一年的沧桑轮回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心灵的升腾与坠落中,都能够默默承受,那是因为心中亮着一盏灯--成功的喜悦与人生的飞扬。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如果没有机缘的相助,个人的艰辛奋斗要走多远才能得到回报?年轻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希望赢得成功,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成功的欢笑与失败的泪水构成生活的两个层面,在由失败抵达成功的进程中,喜怒哀乐相伴而行,构成千姿百态的心情故事。有些梦想是永远无法抵达成功的彼岸的,有些梦想是需要坚持的。朋友对我说,“其实你比我更聪明,何不再考一次呢?”朋友的话使我重新省视自己的生活,认真思考未来的人生走向:无法做到崇高,那就尽力做到平实,决不能自甘堕落,沦于平庸,更不可半途而废。曾经付出努力,勇于拼搏,那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它不会磨灭,也不该磨灭,更不该丢弃。我崇尚那些不断进取的灵魂,我羡慕那些走到成功地位的个体,我理解所有为生命的价值而不懈努力的精灵。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很多,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点色彩,没有一点张扬的人生。
重新捡起书本后的进击,来得格外地踏实。1997年的冬天,我比任何时候都冷静,两年多的机关生活使我学会了保护自己。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拼命看书,恰逢部长换届,新老部长交接的真空中我悄悄地参加了1998年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有意思的是,1998年的夏天,当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中时,我正在参加县委年轻干部轮训班,轮训班结束时,我就是副科级干部了。但我很快乐地离开了那个许多人想进入的机关,一点留恋都没有的彻底的快乐。